你已经走过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此刻你跟我说,现在最想去的是法国。你一直迷恋于蝴蝶,觉得这种幸福的昆虫是会飞翔的眼睛,她的美丽如同你张开掌心时露出的那一片纵横蜿蜒的纹络。
蝴蝶般的船
作者:潘云贵
你已经走过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此刻你跟我说,现在最想去的是法国。
你一直迷恋于蝴蝶,觉得这种幸福的昆虫是会飞翔的眼睛,她的美丽如同你张开掌心时露出的那一片纵横蜿蜒的纹络*。
你觉得世界上最美的蝴蝶一定会在法国。那里有每个季节都会跳华尔兹的女人,她们的身上喷着你羡慕了些许时日的香水,那种醉人的芳香从你开始留起过肩的长发、偷偷穿上母亲银白色的高跟鞋的时候就一直向往。那些女人身上五颜六色的毛绒或是皮革的衣服对你来说,有着巨大而遥远的诱惑。心中安放着一个陈年而精致的术箱,你希望把这些香水和服装放予其中,然后用一把漂亮的闪着剔透日光的小锁锁上。 那时,你会只身一人把这木箱子抬到你蝴蝶般的船上:在梧桐叶开始制造一场浪漫的旅程时,你会坐在蝴蝶船的船桅边,跟着不知从何处吹来又将吹往何处的风,穿越无数条干净细致的街巷和无数座肃穆庄严的哥特式建筑的顶端,远行,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流浪。 晤,我记得你曾经说,忧伤是生命的底色,我们都无可逃遁。蝴蝶在你的心底,亦是忧伤的小生命,轻薄的翅膀在钢筋丛林中游荡,总觉得是一种微小与庞大的对比,在斑斓的纹络里藏匿一生。
就是这样的船儿,你却要执意地登上,并且要将它开过卢浮宫幽深静谧的过道、凯旋门两侧日愈生出的零碎的细缝,或者是你一直都很崇拜的文学家的声音和一直都想看到的那一双双沉睡着却很动人的眼睛。 你偏执地相信,这艘蝴蝶般的船能逾越时空的一切而到达理 想中的口岸。逾越虚妄、真实、古老、理智与轻缓流淌的塞纳河沿岸橘红色的灯光,抑或是逾 越构成这艘小船骨架的忧伤和思想。
窗外的巴黎,此时又是一片不夜城难以低调下来的灯火,窗内是玩累的人群那一排均匀而整齐的呼吸。
白昼绵长的喧嚣里,他们隐没其中扮演各种人生大抵上要经历的角色,或主角或配角, 或上流或底层。而此刻在这座城市的夜色中酣睡的人,他们是平等的,梦也是平等的,没有贴 上用来区别的该有不该有的标签和价格。
若此时换作是你,定然不会叫自己轻易臣服于睡梦中。你会打开一架老式唱片机,放一 张尚·马龙的法语香颂唱片,在接近凝固的安静里撬开平日压抑许久的门锁,临窗卸下一个 自己,一个不像自己的自己。
你开始在窗户上留下一个吻。这个吻是杜拉斯最先教会你的。
孤独、欲望、死亡和绝望,是你扎两个羊角辫露出一脸单纯神色时异常抵触的词汇,像一 只刚刚蜕变新生的蝴蝶面对一个偌大的冬天,掌心无端地生出许多。寒意。一些人希望自己可 以努力地走出杜拉斯的绝望来看她的绝望,走出女人的宿命来看女人的宿命,而你用自己的 一小段蓓蕾初绽的年华证明,这些人会陷得更深,包括你,在无尽的荒野里,奔跑只是徒劳。
第一次看《情人》,是在你12岁的时候。
一整个漫长的冬天,你却没有再收到任何一封她或他的信件。阴冷的风迎面而来,你泛 白的指甲在深红色的铁质小箱前漫不经心地滑过,留下一道细小的指痕。回想起再J一点的 年岁,5岁或是7岁,你每天也都在习惯着无人陪你说话的黯淡时日。父母外出工作,为生活整 日奔波忙碌,他们在困顿一天后的睡梦中也在为你的明天规划。你终日在那栋散发霉味的烂 尾楼的某个边缘的窗户里看着外面的世界,不远处有和你同龄的小朋友在玩大象滑梯,他们 嘴里嚼着魔鬼糖,不时吐出染威了红色或黑色的舌头来吓过路的行人,几个气球不知被谁不 小心扯掉细线,从你眼前飞往云层之上。你鼓着小脸抖了抖安全网生锈的钢丝,它纹丝不动, 你却沾了一手暗红的铁屑。
孤单是你在年幼时便开始圈养的隐形生物,在逐渐成长中,何时将它放归,你未知。
孤独成为你对《情人》的第一印象。当然,还有杜拉斯用来成就爱和欲望的热带殖民地的气息,热带的灿烂,豪华别墅,刺眼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以及夜晚,在浓密的树影之中裸露的无边的黑暗。
拉康说,杜拉斯肯定不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因为她会迷失方向,这将是一场灾难。
你十分认同拉康的言论,因为在阅读《情人》的过程中,你也发觉盼确不知道她在写什么,她似乎只是一味迷失在自己制造的巨大谎言和巨大误解之中。到最后,她只有顺应读者的意思,一宜喋喋不休地诉说着白人少女和中国富翁的故事。
14岁,你开始在青春的腹部里生长,遭到了很多人和事。
知道雨天的时候会有喜欢微笑的女孩和你一同撑伞走过泥泞的路面;知道有-个小胖子总会在心情好的时候把大包的金丝猴奶糖拿到班里分给同学吃,每次分到最多的总是你;知道在你扁桃体发炎的那段时闻里,抽屉的几本书之间会夹杂着一包金嗓子喉宝和一盒塑料瓶装的白色药片;知道在你快乐或者悲伤的时候,总有人会陪你笑陪你哭。
活着,既是过程,又是状态。孤独与失落,一时间从你的心牢里获释。
你发觉自己不能够再爱她了,这个叫“杜拉斯”的女人。她的一生像电影一样掠过你的脑海,她的孤独、絮叨、谎言、酒精和绝望成了你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和对她的一见钟情一样,你摆脱她的决心也是这般突如其来。因为你无法再承受她不堪的一生。 你隐隐约约觉得,在青春的时候,选锴了人生的标签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所以此后的时日里,你再也想不起15岁半的女孩和那个来自中国抚顺的情人的故事,或者说,由他们俩共同演绎的情节,单纯的爱情或者色情。你只记得在小说最后,大洋上的黑夜里放着那段肖邦的圆舞曲。你只记得结尾处那个男人给女孩打来电话,已是多年以后,他在电话里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还有你一直记得的那个留在玻璃上的吻。 这个吻,你现在也一直在重复。你能感受得到,丰沛的绝望和彷徨互相纠缠着,但却在那些晦涩的罅隙里,露出缕缕温暖的光芒。
夜里一个人的苍凉,很快就过渡到了清晨的温暖中。
你说此时你若是起床,便会首先拉起百叶窗,然后打盆清水,花短短的十分钟洗漱一番,便又急急拿起一件素色的外套出门。你受去巴黎圣母院,去协和广场或者某个漂亮的却叫不上名字的公园。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在法国,这一点你深信不已。
看不见的气息夹杂着历史的味道漫空行吟,把石塔、剧场、街道覆盖,潮湿得像下个不停的细雨。你说,若是自己成为路旁某一棵梧桐树-毫不起眼的叶子,定然可以感受得出其中滋味。
城市巴士的玻璃窗上依旧会有你留下的蝴蝶状的吻痕。均匀地落着白色雾气的蝴蝶,它的身后是一排排倒退的树影,还有你一直想看的哥特式的教堂和楼字。
时光挽起巨轮,你的成长也在以一种近乎风的速度向前开去,倒退的是回不去的时光、丛林和某个遗落的微笑。
长大之后的我还会知道有微笑这种表情吗?
你问我的那天,是17岁的末端,面对突如其来的长大,我们手足无措。
而你终究不爱笑了,因为你要靠近长大的尽头。在庞大的人海里,熟稔地习惯每个行人的角色、面具和冷漠,就像你的蝴蝶面对着一个冬天的挑衅。
你好。陌生人。
你会开始用这样的口吻去称呼在你生命行经途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忆的人群,而他们却把整个没有温度的社会交给你。
你好,忧愁。
不知何时起,你成了一只忧愁的蝴蝶,或许是18岁之前的两三年。
那时,你正在沿海上高中,天空本应是一块湛蓝的玉器,在你眼里却是灰色的看不到边际的阴天。
一些昔日同窗有着让人钦羡的家世,他们会在中考一败涂地后摆出一脸不屑的神色对你说,自己近日就要出国,停在国际机场的飞机正在等他,他要去大洋彼岸,去你一直想要游过去的大海的尽头。
一些朋友则承袭着父辈留下的贫穷,茫茫学途对他们来说是一条望而生畏的道路。他们只能执拗地背起沉重的决定,选择用血汗甚至是血泪来改变命运的航向。
他们都将比你早些时候步入纷繁的世间,学着在疼痛中长成像你父母那样沧桑的模样。你紧紧捻着裙角没有说话,因为你觉得这样的选择是最无奈的自我欺骗。他们挥挥手,示意你已经到了离去的港口,你对着这些远去的尚且稚嫩的面孔轻轻说了声,一路顺风,然后悄悄红了眼眶。
曾经的不离不弃,曾经的海阔天空,没有谁会义无反顾地前往。
或许只有你一直在义无反顾地重复简单机械的生活,上课,做作业,吃饭,背诵。旁人说你总是醉心地投入其中而不知东方既白,而你只是在醉心地遗忘,用无尽的循环来遗忘曾经的年岁,说说笑笑拉着彼此的手大声喊大声笑的年岁。
其实,你本不愿这样囚禁自己。
因而,你从娇小的骨子里生出愈见庞大的叛逆和任性,无边的想象和对现实习以为常的麻木。
你会在清晨拒绝母亲的一杯牛奶而空着肚子跑到学校,会为高中班主任喋喋不休的说
教而顿感百无聊赖,会因某个同学不理会你说的一句话而大发雷霆,会偏执地与家人因鸡毛
蒜皮的小事吵上一通,会强行拉着一位近视高达五百度的女伴去附近的商场看LV的山寨
包,而那个女伴的心里还想着今天数学课上的那条弯弯曲曲的抛物线。
你总是笑着告诉我,跟《你好,忧愁》中的塞西尔相比,你的任性是多么的渺小与脆弱。它
们在骨子里翻江倒海地作怪,却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而塞西尔的任性却要陪上一个叫
“安娜”的女人的生命。
任性的力量是可怕的,特别是青春期里沸腾的任性。
你一直在想,塞西尔的任性与罪恶的源泉在哪里?毕竟她才17岁,和你年纪相仿。
不想提弗洛伊德,但是他的确在上个世纪初和马克思一起平分了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
论的天下。
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恋父和恋母几乎在所有少男少女的心底埋藏着。母亲自女儿
出生之日起,就会暗暗将女儿置于竞争者的地位。而作为女儿的塞西尔面对即将成为自己母
亲的安娜,内心的仇恨可想而知,她不想让父亲西蒙接受这个女人。所以她开始了激烈而恶
毒的反抗,设下一个圈套,让安娜失去了自己最为重要的西蒙后出车祸死去。
罪恶是现代世界中延续着的唯一带有新鲜色彩的记号。
塞西尔说,我考虑着要过这种卑鄙无耻的生活,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忧愁。
18岁的萨冈就这样为你营造了这种残酷的忧愁,不解青春、不解人生、不解结局的忧愁。
其实你很怀念“萨冈”还没出现时那个瘦弱的小女孩。她踏进法国朱利亚出版社的大门,
神情略带羞涩,在手稿外面的黄色信袋的右上角写着:弗朗索瓦丝·古瓦雷,马莱布大街167
号,1935年6月21日出生。
可是后来你发觉,堕落和沦丧会是一件非常快、非常容易的事情:世界的变化,原本在50
年不到的时间里进行完毕。
古瓦雷不见了,“萨冈”用近乎冷色调的人生取代了她:年少成名,彼时青春美貌,与若干
大人物有染,喜欢酒精、赌场、跑车和勃拉姆斯,吸过毒,甚至进过监狱,最后晚景凄凉。临死
前已经撰写好自己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不再为此感到痛苦的,弗朗索瓦·萨冈。是的,她早
已遗忘那个最初的名字,弗朗索瓦·古瓦雷。
普鲁斯特告诉你:在记忆的长河上,我们无法站在现时这一点上。然而有人告诉我,如果
我们回望过去,过去只有痛苦和背叛,我们是没有希望的。记忆里只有落日时分的人,不会对
明天即将升起的太阳有任何憧憬。
我想和自己和解。
这是《你好,忧愁》里唯一让你心动甚至心疼的句子。
所有的青春都必然包含一定的赌气成分在里面。无来由的抗争,和成人的世界、秩序的
世界,和这个约定俗成、长大后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够抗争并且得不到胜利结果的世界。
用了一生的时间去成长,一个人却始终无法与自己的青春和解。
萨冈就像一只黑色的蝴蝶,贴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发出隐隐的疼痛。
巴士到站后,你定然不会搭乘的士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你会慢慢挪着小碎步去往协和广场。
好的景致就像一杯好的咖啡,也总要人细细地品,方才体悟到其中滋味。
鸢尾花攀附着欧式墙壁倾听你的心事,你的心里竟有些莫名的惴惴,想来或许是故地与
异国的距离加深着你的奔波与苍凉之盛。年少时听人说,鸢尾花会在无人途经的午夜唱歌,
那时四处藏匿的鬼会哭泣着来到花下,有一段时期你听完这件异事,手指居然无端地颤抖起
来,怕得要死,连白天都不敢一个人打花下走过。
年华灼灼,这中间空缺开来的多少人事,成为一方小小的汪洋,漂白了你曾经的畏惧与
可爱,如今皆淡如裙裾狭处一袅浮青暗纹,远得看不分明。
协和广场离车站不远,你很快就用目光丈量完了这段路程并且嘴角翕动地来到目的地。
看得出你的惊喜,以及兴奋。
广场呈八角形,中央矗立着一座有3300年历史的埃及方尖碑,那是埃及总督赠送给查理
五世的礼物。碑身由粉红色花岗岩细致雕出,上面刻满埃及神秘的象形文字。广场两侧各有
一个喷泉水池,游人常坐于其旁的石屏休息。
这样的广场,你以为只能在教科书上出现。它精致得形同你看过的某个男子高挺瘦削的
脸颊,藏着几个世纪都欲说出却只想你去猜度与获知的一语成谶。
鸽子寂寂地从斑驳的地面飞向阳光淌下的地方,此时广场人群涌动,人们纷纷脱下礼
帽,表情专注,目光盯着一处。《马赛曲》沉郁而壮阔的旋律在耳边响起,那面从左至右迎风飘
扬的蓝、白、红垂直排列的三色旗,是他们久远的法兰西岁月,是他们盛大而忠贞的信仰。
这样肃穆的场景让你不由想到“流浪”这个词。在北纬48.52度、东经2.2度的地方想念自
己的国家,这是流浪;看着别人的孩子簇拥着他们亲爱的母亲,这是流浪。
原来,你一直都在流浪。
蝴蝶太美丽,流浪的她飘得太忧伤。忧伤也是你眼角卸不下的底色。
你想起了勒·克莱齐奥。在两年前,他闯进你的原野,用《流浪的星星》征服了你这匹孤独
的马。
闲暇时,你在网上看到过他的照片,以及采访的新闻稿。
那是一个谦和礼让的男子,年老后脸庞依旧精致。他的表面温和平静,内心却充满了张
力。而他的眼睛,竟然可以像男孩一样清澈透明,像树荫下阳光照不到的一潭深泉。
瑞典文学院将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莱齐奥时的评语是:“将多元文化、人性和
冒险精神融入创作,是一位善于创新、喜欢诗一般冒险和情感忘我的作家,在其作品里对游
离于西方主流文明外和处于底层的人性进行了探索。”
这种冒险便是流浪,这种流浪便是探索。
潜意识里,人们几乎都希望沐浴在阳光里,希望与社会和睦相处,希望被所有人爱,包括
柏油路上开过的每辆车、车里的每张脸。可只要谈及付出,他们又变得异常怯懦。他们害怕无
法承担起这样巨大而丰盛的责任。于是,他们变得淡漠且缺乏热忱,热衷物质,精于算计,挣
扎在世界尽头。
他们一直都在流浪,被迫流浪。
长大之后,内心里时常会涌起无边的彷徨与迷茫,就在眼前的烂尾楼的某个房间里,你
突然之间发觉已经撑不起“家”的概念。四面是高墙环绕的楼宇,安全网划分成细碎方格的天
空,失去了影子和心灵的人们,绵延悠长的昼夜,万物俱归于岑寂。
你所谓的“家”,已经飘到遥远的地方,你和一个叫艾斯苔尔的女孩都在寻找。
应该说,是从克莱齐奥开始,你相信,也许出走、离开、流浪是回家的一种方式,至少在出
走、离开和流浪的背后,藏着回家的愿望。
流浪之前的幸福时光,流浪,逃亡,永远找不到家的悲剧。结束流浪的希望仿佛神话里珀
涅罗珀在纺车边织寿衣等待奥德修斯的归来,她白天织晚上拆,生存所呈现的循环方式在此
重新得到希望。如果我们相信神话模式的毒咒,人也许是注定要流浪,且一旦走出家门,就似
乎永远回不去了。
而克莱齐奥成了少数的能够回到自己家的人。
而你也想跟在他身后,成为少数再少数能够回家的孩子。
你知道,会有一个女孩很像你,用天真的流浪寻找着家,她叫艾斯苔尔。
我曾经问过你,《流浪的星星》里有什么隐喻?
你说是泪水回到了流浪的原点。在事隔40年之后,艾斯苔尔重新找回了泪水,她终于得
以远离漫长的无所寄托的旅途。
泪水是我们最初便想要追寻的事物吗?
你不知道,不过,在艾斯苔尔将父亲的骨灰撒入草坡的时候,你相信,至少她可以不再流
浪。
我知道,事隔多年以后,你也能清楚地一字一顿地背出藏在《流浪的星星》里的那首诗:
在我弯弯曲曲的道路上
我不曾体会到甜美
我的永恒不见了
协和广场上的人群逐渐散去,你脱下那件晨起时为了抵挡寒气所穿的素色外套,把它轻
轻搭在左手的胳膊上,上面有小小的皱褶。
你想起《蝴蝶夫人》里也有这样一件满是皱褶的衣物,不过它的做工和纹络比自己的这
件好看许多,就像是真的蝴蝶。
露水从栏杆上滑落,变得不再冰凉,璀璨明亮的日光中生出轻盈透明的小翅膀,像蝴蝶
般的船。
其实,你一直都在想象着自己应是坐在了这艘小船上游历了各个国家,听过了许多文学
家的声音,和看过他们沉睡的美丽的眼睛。
阅读多少遍描述法国的文字,不如亲眼看一下这个国家。
你说,法国三面环海,大部分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四季宜人。你可以去看看我还没到过的
阿尔卑斯山、科西嘉岛、埃菲尔铁塔,也可以去听听那些20世纪以前的文坛巨匠的声音,比如
雨果,比如大小仲马、福楼拜、普鲁斯特和纪德。
你说,那么请你坐上这艘蝴蝶般的船,择日前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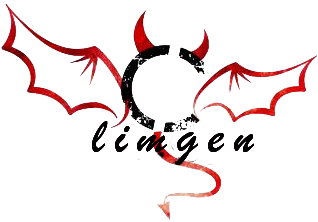






评论